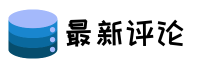因此,尚不清楚根据第 62 条作为一方当事人提出介入申请是否应导致法院对第三国施加适用于提起案件的国家的可受理性标准,例如援引其他当事人责任的资格。如果是这样,那么基于一国在履行普遍义务或普遍当事方义务方面的共同利益,承认其作为一方当事人根据第 62 条介入可以说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它可以依靠这一基础以新案件的形式提起这些诉讼。然而,同样可能的是,法院可能会抓住机会,仅根据第 62 条的既定要求和与当事人的司法联系来评估此类请求,。
尼加拉瓜有着丰富的介入经验
这包括寻求参与尼加拉瓜诉美国和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的第三国,以及在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的上述分庭 手机号码列表 中开创性地出庭。在本案中,尼加拉瓜将其作为当事方介入的申请与《规约》第 36(1) 条联系起来,(¶1) 从而将《灭绝种族罪公约》作为其与南非和以色列的管辖权联系。如上所述,这也许是它根据第 62 条关于《公约》“所有缔约国”的“共同利益”进行介入的唯一方式。(¶10, 14)
然而,尼加拉瓜声称其请求“涉及
《公约》的适用或履行,也涉及与《公约》的适用密不可分的《公约》的构建或解释”,(¶16)从而将第 62 条和第 63 条与其各自的 另请阅读 如何处理市场上的评论 历史起源分离开来,并对这些条约条款进行了相当难以区分的解释。作为国家了解其已成为缔约方的条约解释的一种机制,第 63 条植根于国际仲裁以同意为基础的起源,并可从 1875 年国际法学会决议、1899 年和 1907 年设立常设仲裁法院的公约以及 1907 年国际赏金法院公约草案和 1910 年议定书草案中找到明确的先例。相比之下,第 62 条是海牙法学家委员会在起草 1920 年《常设国际法院规约》时创新的,旨在确保这个史无前例的全球法院在解决其他国家之间的争端时不会侵犯第三国所声称的权利。虽然公约的制定显然会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法律利益”,但第 62 条因此反映了与第 63 条不同的历史原理,这导致法院在其判例中赋予其特殊含义,并在其《法院规则》中采取不同的方法。
尼加拉瓜的申请书中有几点令人怀疑其根据第 62 条而非第 63 条进行干预的有效性。在这方面,尼加拉 香港领先 瓜试图通过更新“当前局势”的事实记录来增加价值(¶6)——尽管尼加拉瓜引用的资料来源通常属于公共领域(¶4),南非仍然有权向法院提供此类信息。鉴于第 62 条请求(而非第 63 条声明)的自由裁量性质,值得回顾的是,法院过去曾以第三国已通过申请本身表达其利益为由驳回此类请求。